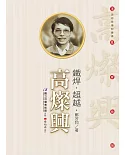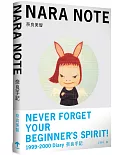張大千先生詩書畫,名溢海內外,世皆許其為五百年來第一人。彼岸當道,久望羅而致之內江故郡,顧大千所眷眷者,為首丘臺員。蔣經國先生曾屬予為之相其土宜,商其堂構,卒以外雙溪合流處景物最勝,經之營之,遂成「摩耶精舍」一區,雖土階木椽,已復繞屋栽梅,聊可行吟伸紙作畫矣。其間曾成廬山高及江山萬里圖,為其平生劇。大千既逝,營奠營喪,一委之予為之區畫。大千嘗有句云,「綴玉苔枝乞百根,橫斜看到長成?,慇懃說與兒孫輩,識得梅花是國魂。」隨後又有句云「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墮淚倍思家,眼中多少頑無恥,不認梅花是國花。」益感不絕於其心矣。遺蛻火化後,即置之梅丘梅花樹下,歲月奄忽,遂復三十星霜矣。其間予曾為其輯印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又嘗於故宮博物院舉辦「張大千與畢卡索的世界」聯展,並版行專輯,或者無復遺恨。頃王家誠先生蒐大千生平,為之傳記,顏曰「畫壇奇才張大千」。其實大千之詩文,大千之法書,自見其盤錯倔強(一作磅),不獨以畫爭奇於五百年間也。甲申歲首,予與林百里先生瞻謁精舍,並禮於梅丘,行吟得句云,「鶴自恓惶柳自斜,菜單畫稿久籠紗,雙溪長憾人長往,不認梅花是國花。」感時濺淚,從可知已。--甲申秋吉 秦孝儀心波玉丁寧館樓居
還原張大千的真實人生 王菡
在本書〈前言〉中,作者王家誠先生開門見山的說:「張大千傳,並不在我的寫作計劃之中!」 多年來,王先生一直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文物》月刊連載中國藝術家傳記。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故宮舉辦「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討論「南張北溥」的生平和藝術。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認為張大千傳已有人寫,而溥心畬傳尚付諸闕如,因此邀王先生執筆。
當《溥心畬傳》開始在《故宮文物》月刊連載之後,王先生就著手蒐集整理下一部傳記──《揚州八怪傳》的資料。未料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溥傳刊出已逾三分之二時,秦先生忽然又邀他寫張大千傳。對此,王先生個人的揣測是:「藝壇上一向有『南張北溥』之稱,溥張二氏不但是馳名國際的近代藝術家,生前均與故宮博物院關係密切,謝世之後藏於該院作品及文物也極為豐富,並曾於八十二年六月下旬,由故宮舉辦盛大的『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成為二氏作品收藏和研究的重鎮;孝儀先生邀稿的原意,或許就是想使『南張北溥』作品與傳記能夠兩全。」
比較寫作溥、張兩傳的不同,王先生認為:由於自己曾親炙溥氏;寫作溥傳期間,溥氏的門生故舊亦提供了許多文獻及口述資料。再加上自己少年時住過北京;為寫溥傳,特別舊地重遊,一一探訪了溥氏的故居和遊蹤──恭王府、頤和園、戒壇寺……因此,溥傳寫來格外親切。而張傳就不同了:張大千生平交遊廣闊,子女眾多。但由於其親族及門生故舊散居大陸及海外各地,未能直接訪談;因此,寫作時主要還是藉重文獻資料。
這點對他而言並不構成困擾,之前寫明、清時期的畫家傳記,不也是如此?問題在於:張大千的資料極為繁瑣龐雜,整理起來無非是千頭萬緒!
寫作張傳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張大千傳已有多人寫過;要怎麼寫才能另闢蹊徑呢?他接受了妻子,也是著名散文家趙雲女士的建議,從張大千的敦煌之行切入。所謂敦煌之行,是指張大千自民國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一年)起,帶領家人及工作人員在敦煌摹寫石窟壁畫的艱辛歲月;歷時共兩年七個月。
由無垠的沙漠所展開的史詩般的壯闊場景,這樣的開場無疑是戲劇化的;而可寫的題材也很多:有敦煌的大漠風光,石窟中的藝術瑰寶,藏人的民情風俗,悲涼詭異的「將軍斷手」故事,哈薩克人的襲擊……
不過,這趟旅程也是惹人爭議的;爭議點有二:其一,張氏此行有無任意剝落壁畫,盜取敦煌文物?其二,部分人士認為,敦煌壁畫中那些色彩艷麗的宗教繪畫,乃出於工匠之手,並不值得學習;有人甚至說了重話:「畫家沾此氣習便是走入魔道,乃是毀滅自己!」
對於以上種種爭議,作者在仔細比對了各家說法,並審視張大千日後在藝術上的表現,作出了以下看法:「將近三年的敦煌面壁,鑽研和臨摹北魏隋唐壁畫,是他(張大千)在藝術發展上承先啟後的關鍵。在發揚中國古代繪畫、雕塑藝術,促使國人以及世界注意敦煌藝術寶藏、積極進行保護和研究方面,均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故擬由此作為大千生命史詩的切入點。」
作者王家誠先生,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專攻近代西洋繪畫。喜愛文學的他,除了繪畫之外,也受當時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和散文。大約民國四十幾年,電影「梵谷傳」及余光中先生翻譯的《梵谷傳》,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想到我國藝術家的傳記,往往只有短短幾百字,乃至幾十字,便概括了一生。完全無法表現一位大師多彩多姿的生平,藝術思想的形成以及承先啟後的脈絡。如果能像西方藝術家傳記那樣,蒐集完整的資料,經過系統的分析、整理,然後以活潑、生動的筆調撰寫出來,那就會大不相同了。
從他的初發心之作《中國文人畫家傳》到現在,匆匆三十多年過去了。這期間,他發展出了一套縝密的研究方法。而他學術性與可讀性並重的寫作手法,也為中國畫家傳記樹立了典範。
現就本書的特色以及作者寫作本書時所持的基本立場略加闡述:
首先,本書不僅內容翔實,描述得也很生動;好像作者當時就在現場。這要歸功於資料蒐集的完整。以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例:前面說過,作者為了寫溥心畬傳,親自到北京去探訪溥氏的故居。然寫張大千傳時,作者已年近七十。身體狀況不允許他遠赴敦煌大漠。為彌補此一缺憾,他多方蒐集敦煌的相關資料;更先後參觀了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及臺北歷史博物館舉辦的敦煌展;在模擬的洞窟中體驗臨場感。
其次,張大千的資料繁多;有時各家的說法難免不一。在仔細比對各家說法後,如能還原真相則還原;如有疑難則兩案並陳。 對於張大千惹人爭議的部分,如他豐富的感情生活及造假畫一事。作者不隱諱、不渲染也不評論,只以「說故事的人」的身分將事情的始末娓娓道來。相信讀者心中自有一把尺,功過是非就由讀者自己來論斷。
本書於正文後,亦附有年譜。張大千的年譜曾有多人編寫;本書的年譜究竟與其他年譜有何不同?在年譜的「前言」部分,作者作了說明:「張大千書畫及詩文創作的數量,異常豐富。有關他的論述書籍,和當年報章雜誌的報導,也多得難以計數。各種相關書畫冊、著作中,不少附有年譜。為數可觀的年譜,繁簡不一,記述他的生平事跡,更仁智互見。筆者近五六年間,廣蒐兩岸資料及報章雜誌報導,詳參他的詩文、書畫題跋、理論及各種書籍報導,潛心於張大千傳記的研究和寫作。進而就既有的年譜及文字資料、訪談記錄編成〈張大千年譜〉,並逐條註明出處,以備讀者進一步考證張大千傳奇的一生、思想、藝術造詣,及對於近代國畫所形成的影響。」
本書作者王先生為一性情中人,因此在傳記寫作上不僅作客觀的論述,同時也往往將自己的生命灌注於其間。作者本人在藝術創作上雖以西方水彩畫為主,其布局及意境卻深受中國文人畫的影響。另外,在生活上,他喜歡享受在平靜中點染的小小樂趣。因此,當他在從事傳記寫作時,常選擇藝術理念及生活態度和自己較為接近的對象;如之前的《鄭板橋傳》(九歌版)、《吳昌碩傳》(故宮版)、《明四家傳》(故宮版)、《趙之謙傳》(歷史博物館版)等等。張大千在許多方面和他從前傳記的主人翁大異其趣;因此,對他而言,寫張大千傳也算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但同為藝術家,他不難體會的是張大千對藝術的熱愛與用功之勤。藝術是藝術家的生命。也唯有如此,其作品才具有生命力,也才能贏得他人的欣賞與共鳴。
另外,本書作者和張大千可謂「同病相憐」。他二人都深受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眼疾所苦。失明對畫家而言,就像耳聾對音樂家一樣,都是再殘酷不過的事了。張大千有幸如日本方外異人士和田所預言,終生並未失明;反而發展出了風格獨具的潑墨、潑彩畫。王先生除了畫畫之外,寫作也是其工作重心之一;很難想像,因白內障及視網膜病變而導致視力嚴重受損的他,在閱讀時,除了一副老花眼鏡外,手裡還要拿著高倍放大鏡。這對於要閱讀大量資料的他,真是苦不堪言。但也或許如此,使他對張大千晚年老病纏身的晚景與人書俱老的境界,體會尤深。
王先生常歎,自己的傳記文學不如一些歷史小說來得受歡迎。或許,這本《畫壇奇才張大千》不像稗官野史那麼戲劇化;卻絕對忠於事實。張大千的一生本就多彩多姿;他妻妾成群,喜愛修築園林,蒐集奇花異草,豢養珍禽異獸;他惹爭議,也有冤情;他「富可敵國」,卻又「貧無立錐」。而作者的生花妙筆則能幽默、能狂放、能圓熟、能蒼涼;寫盡書中主人翁傳奇的一生。剩下的,就只待讀者的細細品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