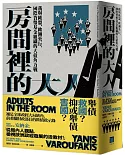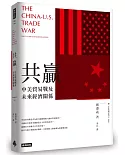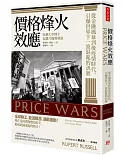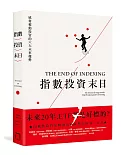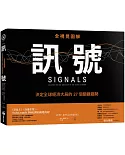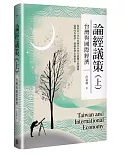揭開葛林斯班的光輝面紗南方朔
顯赫的要人有兩種:一種是遺愛人間,長留去思;另一種則是在位時由於位高權重,加以長袖善舞,因而一片阿諛歌頌之聲,但因他並未嘉惠於民,一旦離職,非但繁華落盡,甚至還會被後人追著數落,在位和離職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景。
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理事主席葛林斯班,儘管在位時,由於美國十二兆美元的經濟規模,使得他有了「全球僅次於美國總統,擁有第二大權力」之稱,但他於二○○六年一月卅一日任滿離職後,他的評價顯然不會是「遺愛人間,長留去思」這一型,或者也正因此,他遂於離職前的二○○五年八月,柬邀全球主要國家的央行總裁和重要經濟學家,參加在美國懷俄明州為他舉辦的「向葛林斯班致敬討論會」。在一片阿諛歌頌的言詞裡,只看得到現實官場的趨炎附勢,這反倒給人一種不安的預兆。
如果我們注意近年來的美國財經評論,當可發現到自從美國高科技股市泡沫破裂,一九九○年代所謂的「新經濟」宣告結束後,葛林斯班的神話即已開始褪色。所謂的「新經濟」,指的是一九九○年代美國透過新科技和新金融而造成的階段性繁華假象,而實質上則是透過國際借貸來促進需求的「非理性繁榮」,當時葛林斯班還信誓旦旦地向柯林頓總統表示:「目前的經濟狀況,是我在五十年來見過最好的。」他的話更助長了當時股市最後一波投機潮。但不旋踵,股市即告崩塌。從此之後,葛林斯班的風華即開始漸趨凋零。美國財經評論界甚至還出現了兩個帶有貶意的專門名詞,一個是「葛老如是說」(Greenspeak),指的是葛林斯班那種故意模糊、閃爍、迂迴,聽起來讓人正反不分的談話風格;另一個則是「葛老經濟學」(Greenomics),指的是他在決策上那種自我矛盾,非常機會主義式的經濟學概念。
對於「葛老如是說」和「葛老經濟學」,在此可以舉一個最新的例證。今年(二○○五年)七月,自從高科技股市泡沫破裂,在低利率房貸帶動下,美國游資自股市撤往房市,造成了將近五年的房市榮景,像某些特定城市如聖地牙哥,屋價上漲甚至高達百分之一一八,房屋價格上漲的程度遠遠大過房租上漲。而今由於利率持續上調,七月起無論新屋或成屋的價格及交易量已開始下滑,加上總體經濟的不平衡,一般的零售也告下滑,於是所謂「房市泡沫」之說開始興起。在八月份「向葛林斯班致敬討論會」上,葛林斯班本人在他那兩千多字的演講稿裡,即這樣說道:
「房屋市場價格的劇漲,有部分原因乃是投資者接受低度風險報償所致。這種房價的上漲,也經常被市場參與者認為是一種結構性和永久性的。……但歷史對這種低風險借貸延長期的後果,卻不會太過仁慈。」
上面這段話就是典型的「葛老如是說」語法。它的意思其實很簡單:過去由於低利率,因而房貸成本也低,投入房市當時低風險,但大家一窩蜂造成的房市狂熱,卻可能成為破裂的泡沫。因而他的話,其實也就是「小心房市泡沫化」。
但我們卻不應忘了,就在二○○三年十月,所謂「房市泡沫化」之說即已甚囂塵上。當時葛林斯班卻極力否認說道:
「雖然各個地方的經濟會經歷到明顯的投機價格不平衡,但全國性的嚴峻價格扭曲卻非常不可能出現。」
他的這句話乃是承認會有房市投機,但卻否認它會變成泡沫。他對於別人的預警拒絕加以承認,等到問題惡化,卻又好像很英明地去說別人說過的話。難怪在他跟著開始說「房市泡沫」後,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要如此指責曰:「他的智者謊話來得太遲,就像是有個人,過去主張馬廄的門應打開,但等到馬跑掉之後,他才發表意見,聲稱把門關好是多麼重要。」
因此,葛林斯班這個被認為是「全球第二有權力的人」,其實是非常值得分析討論的。他過去被人阿諛歌頌,到底值不值得?他參與美國財經決策已有卅年歷史,而擔任聯準會主席也十八年任滿,到底做過什麼樣的貢獻?他的地位,到底是因為他有過人之處呢?或者只是因為美國強大,遂使得他也跟著顯赫?
而所有的這些疑問,現在終於有了答案,美國達拉斯的南美以美大學教授拉斐‧巴特拉(Ravi Batra)這本《葛林斯班的騙局》,即是個重要的開端。台灣的讀者和學者,甚至經理人,都應該對巴特拉教授並不陌生。一九八六年,他那本相當著名的觀測分析之作《浩劫一九九○》(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990),也是台灣的財經暢銷書。該書很準確地料中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大崩盤。他以預測神準聞名,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他做了卅三次世界大事的預測,卅次都準確無誤。這次他形同是在對葛林斯班的財經思想、風格,以及政策做評論,同時也對美國最近廿多年來的經濟變遷和未來做診斷,可以說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反主流著作。在這個美國經濟已千瘡百孔的時刻,這部具有總體回顧和反省意義的著作,不但對美國極具啟發性,對全球其他國家──當然包括台灣在內,也都有財經思想再啟蒙的作用。
如果我們檢視當今的美國經濟現況,就會發現在過去這卅年裡,它已經歷了美國歷史上從未曾有的結構性改變,那就是由於租稅累退,貧富差距已如火箭般被無限拉大;而所謂的「雙赤字危機」──即預算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也達到從未曾有的高點,美國已成了必須仰賴國際社會裡其他國家的儲蓄充當自己消費動力的國家。而美國社會本身,則工作機會幾乎已達零成長,實質工資所得則持續在向下滑落。這是一種嚴重的失衡與扭曲,它已到了所謂的「難以為繼」(Unfulfilled)的危機邊緣,而更嚴重的,乃是這種不平衡的結構,由於它在特定時段裡還是會形成鍍金般的光彩,因而它在許多國家也被意圖複製。因而不但美國經濟泡沫對全球造成極大的長期破壞,甚至可能形成泡沫與泡沫間的連動破裂。
對於這種情況的形成,人們就開始要問,這是何以致之?孰令致之?而更重要的,乃是它是在怎麼樣的一種經濟論述和財經政策下,被導向到這樣的途徑上?
而巴特拉在這部著作裡所試圖論證的,即是這一切都是美國財金不倒翁,經歷了福特、雷根、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五個總統的「五朝元老」葛林斯班所賜。他把劫貧濟富,以借貸製造短期榮景的政策推向了極端,而他的整個經濟論述則是充滿了知識上的詐欺,於是整個美國經濟體制遂被型塑到了一個新的、違背了基本道德與常識性的方向。而葛林斯班那種反反覆覆的經濟論述,即是這種知識詐欺的具體表現。「知識詐欺」,這是嚴重的指控。對於台灣的我們,由於追隨美國主流已久,人們談到葛林斯班時,也都學著美國人一樣的尊稱他為「葛老」,在台灣已有的多本相關主流論著譯本裡,也都是歌功頌德之作。因而乍聽到「知識詐欺」這樣的指控,難免會覺得刺耳。但若我們追隨著巴特拉教授那種長期追蹤的腳步,當會發現到他對葛林斯班的「知識詐欺」指控,容或過分凌厲了一些,但葛林斯班在過去大約卅年裡,尤其是他擔任聯準會理事主席期間的知識與政策操弄,則毫無疑問地應負起相當主要的責任。
由巴特拉教授那本著名的《浩劫一九九○》──那是一本預測蕭條再臨的著作,我們已可知道他的治學方法,大體上可說是歷史制度經濟學的嫡傳,他用這樣的方法來檢證週期循環裡的租稅、所得、投資、供需等各項因素,而後據以判斷未來。這種歷史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基本上乃是要在各個短期經濟現象裡,去探索經濟以及經濟之外的社會、政治,甚至道德因素的影響,它當然也就勢不可免地會在經濟分析裡,不明言地設定出許多批判性的價值標準。這是一種經濟知識理論的前提,當我們一開始有了這樣的理解,就會對這本重要著作裡那經常讓人側目的用字遣詞不以為忤。這是我們在閱讀本書之前必須有的認知準備。
那麼,這時候我們就要追問,根據本書那資料確實、而且主要是透過「聽其言、觀其行」的比對,而後根據「選擇顯示偏好」,而論證葛林斯班所偏好的價值以及決策的意識形態背景,他對葛林斯班的指控是否實在?這時候我們就要非常抱歉地說,他的指控其實是相當確實的。而且這種指控,巴拉特教授也並非第一人。台灣所熟悉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曼即已是葛林斯班的主要尖銳反對者之一。這種指控在當今美國財經評論裡,其實早已成了由非主流逐漸變成新主流。只是以一本著作而做集中式的指控,以巴拉特教授為首而已。
在本書裡,最雄辯的乃是它的第二章「社會安全的詐欺」這個部分,在一九八一年,葛林斯班即建議替富人刪減所得稅和公司稅,同時又以拯救嬰兒潮世代的社會安全制度為藉口增加社會安全稅,而後又逐年放水,讓社會安全基金成為挹注財政赤字的工具;然後又以降低聯邦赤字為理由要求裁減社會安全年金。這是透過各種知識詐欺而玩的「劫貧濟富」遊戲,而就在這樣的操弄下,他從中產階級和勞工手中劫掠了一‧五兆美元來彌補替富人減稅所擴大了的赤字。在這個部分,其操弄的論述和欺瞞都歷歷在目。葛林斯班玩法弄權的本領已具現無遺,其手法也真讓人嘆為觀止。
而除了在社會安全基金的操弄上做了全紀錄的探討外,巴特拉教授並在本書裡詳細分析了葛林斯班那種為富人爭取利益而不擇手段的意識形態起源。師承由來,及其在聯準會理事主席任內以其掌控財金大權的機會,造成了整個美國社會經濟體制往惡化方向的重構。在這些方面,他並從經濟的學理,證明了葛林斯班的光環,其實是透過舉債而建構起來的假象,而其結果則是整個美國付出了財富分配不公的擴大、利率提高、赤字惡化、就業減少、有蕭條之虞的代價,他並由學理證明了,葛林斯班的舉債,乃是以加快的速度擴大了一切的惡化,這是個惡性循環圈,美國已深陷其中。除此之外,許多對葛林斯班歌功頌德之作,都說他任內建立起了聯準會的獨立性,但巴特拉教授卻指出它其實恰恰相反,葛林斯班任內乃是聯準會日益成為替華爾街及富人階級服務的工具。金融是一種手段,有暗藏的意識形態偏差在其中。有關金融手段的意識形態特性,以及它所造成的不良分配效果,個人倒是認為它乃是缺乏政治經濟學思維能力的台灣,最需要去詳細閱讀並思考的部分。
因此,這本《葛林斯班的騙局》,在葛林斯班十八年聯準會理事主席即將任滿離職前出版,其實有做重大的「蓋棺論定」的作用。美國在過去卅年裡,本質上乃是一個為了讓富人追求利益而給予極大化方便的階段。它造成了租稅上的不公、經濟合理性的失落,而富人財富的非理性增加,其實是讓供給和需求落差更大,而各式各樣的泡沫也更加旋起旋滅。這是一本複雜的帳,責任雖然不一定要由葛林斯班全面扛起,但他利用聯準會的職權參與決策、推波助瀾,至少要負起相當大的責任。而為了匡濟時艱,巴特拉教授主張恢復租稅的合理性,調整供需、所得、就業的關係,則無疑地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只是他主張美元持「雙重聯準制」,出口另訂一種價格,那就未免太有爭議了。
目前葛林斯班任期將屆,最近白宮已公開表示,已成立了一個專案遴選小組,尋找繼任人選,被點到名的,計有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務長胡巴德(Glenn Hubbard),四十六歲。費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哈佛大學教授,六十五歲。柏南克(Ben
Bernanke),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五十一歲。但美國財經評論界幾乎相當一致認為,在美國經濟千瘡百孔的此刻,下一任的艱鉅將甚於從前。葛林斯班參與美國財經決策卅餘年,丟下一堆由於結構重塑而造成的難題,看著美國的這些問題,它那種劫貧濟富的租稅政策,它那種圖利富人的經濟方案和財政赤字手段,不也同樣值得我們警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