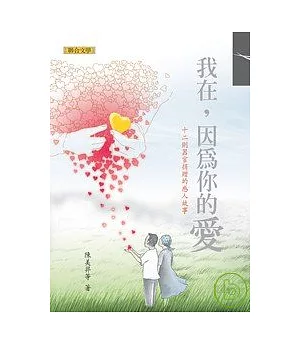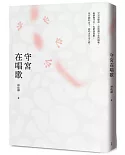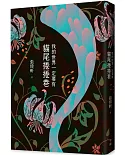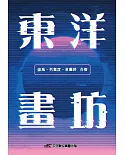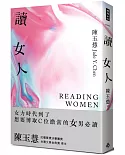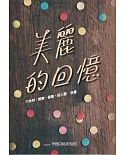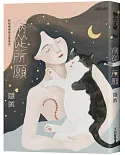發揮無用之大用 證嚴法師
人生,最後一口氣吞下去就結束了,人往生之後軀殼要怎麼處理呢?
土葬好嗎?其實,遺體放在棺材裡會腫脹潰爛,埋在土裡被蟲侵噬,奇臭無比;至於火葬是不錯,只是被推進火爐,也只不過化成一堆骨灰。
假如是我,我很希望自己到了那一天,還能夠有所用。
曾有人問:「佛教說往生以後多少時間內不可以移動亡者,若捐贈遺體或器官是否違背佛教的道理?」
其實,這都是後人的論述,如果探究原始教典,佛陀並沒有說人往生之後多久不可移動。而且在《本生經》裡,都記載佛陀過去生如何獻身救眾生,例如割肉餵鷹、捨身飼虎;這就是佛陀的心願。總之,關鍵就在「心願」,有心有願就會歡喜;能達成心願,更是歡喜。
人斷氣之後,若身軀被移動會不會很痛苦呢?近代有一些佛學論者,書中形容死後神識脫離軀體像生龜脫殼、像活牛脫皮般的痛苦,所以人剛往生時不能移動他,以免增加亡者的苦惱。其實,這樣的解釋只分析到第六識。
以佛教來講,人還有第七識和第八識。第六識是分辨與想像;第七識是思考與決定;第八識則是業識種子的倉庫。以中國造字分析:外在的「相」,如杯子、白紙等相,映在「心」中叫做「想」,亦即第六識。而「心」上一畝「田」,心靈的耕耘叫做「思」,亦即第七識。我們接觸日常生活的外境,產生第六識的分辨與想像,然後由第七識思考與決定──回憶過去、想像未來,經過很久的時間還是記憶猶存。
有了心的耕耘,即第七識的思考與決定,接著就會付諸行動。俗語說:「好人總是做好事,壞人總是做壞事。」其實,是因為平時心靈的耕耘,而形成習慣性的動作模式,這就是經過思考和習性薰染之後而造作出來的。有了行為造作,必定形成種子,在醫學上稱作基因,佛教中即稱為「業種」──業力的種子,也叫做「因」。這個種子,這個因,簡單稱呼為「業識」或「第八識」。
人往生之後,肉體便開始壞散,但業識仍徘徊在身體周圍尚未遠離。所以在此時助念並說些安撫的話,以維護臨終者的安寧。此時要捐贈大體或器官,如果是自己很歡喜要捐,這是他的願,願力會提昇意識而超越,他的心識不會起瞋怨煩惱,反而會有達成願望的歡喜。
如果是自願捐贈的人,醫師在移植他的眼角膜或心臟時,他會覺得:「肺也行啊,肝也行啊,這些都拿去用,免得浪費了。」這種成就願心的力量就是功德。不過,我要強調,為保留往生者尊嚴,不要將他的身體翻來翻去,讓他很有尊嚴和安然的感受。
總而言之,一個人最大的意義就是有使用權的時候。世間的一切,包括我們的身體。說生病就生病,即使你不喜歡也沒有權力說我不要生這種病。哪有什麼所有權呢?或者哪一天我們世壽盡了,也不能說:「等一下,我還有某某事沒做,不能死。」一點也由不得你啊!
其實,我們來到人間,最消福的就是身體;要吃最好的、營養的,要穿名牌才有派頭,要睡舒服的床......。由於迷失了正確的生活,迷信在自己的衣、食、住、行,所以就盡量消費,糟蹋一切的物資。然而,這個身體是否真正屬於我呢?我認為當我能使用它,能夠付出的時刻是我的,甚至到了最後一刻,奉獻遺體來救人或供醫學研究,我想這才是真正擁有。
諸位,生在人間,得之於人者太多,我們應該懂得惜福,即使往生之後,身體還可以廢物利用。人生只是生命輪迴其中的一段緣,這段緣要怎樣運用?一生的情愛要如何看待?有的人捨不得世間的情緣,其實最後還是得捨。既然得捨,捨了之後怎樣運用實在值得思考,如果是我,我也希望能捐贈器官或醫學解剖;有誰需要我的器官就讓給他,有此因緣也是一件好事。
我們每天的睡眠如同「小死」,等到一口氣呼出去不再回來,那就是「長眠」。如果有人臨終前很期待奉獻遺體,就應該成就他的心願。能夠做到人圓、事圓、理圓,那就皆大歡喜了。
代序1
再生緣 陳美翌
除夕。
李明哲開著車,載著妻子和三個兒女(當時老四還沒出生),從高雄岳父母家出發,經高速公路北上。很久很久沒回家了,終於盼到一年一度的年假,可以回去和家人吃個團圓飯,李明哲心裡「暖暖」的。
到達瑞芳家裡,手機響起:「李醫師,那個車禍腦死病人的家屬,同意將他做器官捐贈,你快回來吧!」
李明哲二話不說,立刻搭火車回花蓮。
摘除器官、再分別將兩顆腎臟「種」到受贈者的後腹腔內,三檯手術做完,已是大年初一。在確定受贈者術後狀況一切順利後,李明哲才再搭車回瑞芳老家。
「我們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會有捐贈者。」身為東台灣唯一的器官移植醫師,李明哲必須隨時待命:「那是我的天職。」
加入器官移植小組
1991年,李明哲自台北醫學院畢業,就到花蓮慈濟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對血管手術有高度興趣的他,經常?洗腎病人做動靜脈廔管,深刻體會洗腎病人的苦。因此當慈濟醫院成立「器官移植小組」時,李明哲就加入團隊,希望能為病人帶來另外一線生機。
1996下半年,李明哲到台大醫院去跟李伯皇教授學習腎臟移植。除了手術,還學習病人的選擇、術後的照顧、用藥......
1997年四月,李明哲在花蓮慈濟醫院執行了首例腎臟移植,為了慎重起見,還敦請台大胡瑞恆、蔡孟昆兩位醫師蒞臨指導。
「移植之後,我們讓兩位病人住在燙傷加護病房,我就在值班室徹夜守候。」第一次「主刀」的李明哲,又緊張又興奮。所幸手術過程非常順利,患者移植後,馬上就能排尿,令他信心大增。
第二個禮拜,又有一例捐贈的腎臟進來,李明哲真正獨立完成移植,手術的完美成功,讓他覺得「選對了路」。
九月,慈濟醫院送李明哲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醫學中心進修。在那裡他跟著全世界第一個做肝臟移植的湯姆士史達佐教授( Thomas E Starzl)及其團隊學習各種臟器移植。
除了臨床,還參與實驗,或到外地去拿器官:「美國器官捐贈的網路非常成熟,器官的保存、利用、分配都很有效率、很公平。」
台灣過去沒有網路,無法對捐贈的器官做最有效的運用,殊為可惜。但近一、兩年來衛生署成立了「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在互信的基礎上,算是向前跨出一大步。
移植肝臟大考驗
做了多力腎臟之後,2003年,李明哲做了首例肝臟移植,非常順利成功。他開心的告訴當年器官移植小組的負責人,也是現在大林慈濟醫院的副院長簡守信說:「我做到了!」
「我感恩慈濟,送我出國進修,給我機會和好的環境,提供經費、設備......。」李明哲說:「慈濟是一個很特殊的醫院,沒有包袱,但有人情味。只要醫師願意做,醫院都會配合,比如挪床位等。總之,排除萬難,以拯救病人為第一優先。」
同年五月,第二例肝臟移植時,李明哲就碰上大考驗。
那一天下午四點多,接到有車禍腦死病人器捐的訊息,李明哲就率隊南下台東,來回七小時的車程,加上摘取器官手術,回到花蓮已是凌晨三點。
李明哲立刻前往病房探視張姓受贈者,確認移植意願,並告知手術可能的風險。所有的檢查做完,清晨七點,病人送進開刀房。
「我們發現張先生的血管裡的栓塞子太多,清到很深的地方,還是有,怎麼辦呢?」李明哲說:「手術前的評估再怎麼精密,還是會有意外發生。」
血管接不起來,或血量不夠,「新肝」就會壞死,病人也就沒命了,這可是生死一瞬間哪。
「移植團隊『僵』在那裡半個小時,束手無策,欲哭無淚。」李明哲說:「『新肝』的門脈要接到受贈者的門脈,結果『門』都沒有,急死人了。」
此路不通,另闢途徑,最後在靠近脾臟處找到一條大側枝靜脈血管。李明哲喜出望外,用最快的速度將血管接好,看著鮮紅的血液滔滔流進新肝,大家才如釋重負。
這個手術,又處理了病人的腸沾黏及側枝循環等問題,總共耗時十四個小時。李明哲一直等到病人甦醒後,才安心回家。此後三天,除了到醫院巡房探視病人,其他時間都在家裡睡大覺補充睡眠。
「感恩讓我碰到如此棘手的案例,檢查不只做電腦斷層,還要做核磁共振。手術前一定要仔細、做好周全的準備。」李明哲說:「還要有很多種『備案』,隨時應付不可預知的狀況。」
連續四檯刀的「不可能」紀錄
「我可能是一個比較自戀的人,我努力多學,再運用所學去多幫助更多病人。我希望能多做一些,解決病人的痛苦。」李明哲說。
除了挑戰高難度,李明哲也挑戰體力。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斷的打破自己的紀錄。
「過去一向就是摘一個器官、再植入一個器官;2003年,慈濟中學職員彭先生車禍往生捐出全部器官,我從捐贈者身上摘取了一個肝和兩顆腎臟(骨骼由骨科摘取),之後我又為兩位病患分別植入了一個肝臟及一顆腎臟(另一顆轉送大林醫院),一口氣做了三檯手術。」
2004年,來自越南的阮小姐也因車禍腦死,丈夫忍住悲慟讓她遺愛人間。李明哲更創下「摘器官、植入一個肝臟、再植入兩顆腎臟」的連續四檯刀的「不可能」的紀錄。
超過二十四小時,馬拉松式的手術,雖然年紀不到四十,正是盛年的李明哲,還是累癱了。「這樣的紀錄,不是證明我有能力;而是有毅力。」李明哲說:「病人是苦苦等待,我能不做嗎?」
不過這樣「單兵作戰」、「校長兼撞鐘」的局面,很快就會改觀。
「『大師兄』何冠進目前在日本;『二師兄』伍哲遜在台大,兩人都是李明哲的『高徒』,目前也都在接受器官移植的訓練。」泌尿科第四年住院醫師陳景亮說:「等到大家可以獨當一面,『老闆』就不必那麼辛苦了。」
開刀,是一種信仰
慈濟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的陳景亮,和器官移植小組的成員私下暱稱李明哲為「老闆」;又自稱是李明哲的「叛徒」。因為他曾經選擇一般外科半年後,才轉到泌尿科。又緣於對器官移植的興趣,在徵得科主任郭漢崇的同意後,再拜在李明哲名下,學習器官移植。
陳景亮說,李明哲是一個很「迷人」的醫師,在實習時,他就很受同學歡迎:「他戴個黑框眼鏡,酷酷的,但是開刀時,眼神是專注的、自信的、篤定的,散發一份特有的光芒。」
「跟李醫師的刀,好像跟他去旅行。一刀劃下去,就好像火車開動了,要出發囉!」陳景亮說:「李醫師身手俐落,清清楚楚,宛如行雲流水,順暢無比。」
但是李明哲的「脾氣」,也是眾所週知的急。在開刀房,經常聽他「吼叫」。陳景亮說:「他動作快,別人若跟不上,他就會跳腳。或是護士遞錯器械,他也會不耐煩。有時他會跳出來親自『示範』,告訴護士『要、這、樣、拿』。」
陳景亮也曾挨罵,但他被罵得心甘情願。他認為李明哲對事不對人,不會做人身攻擊,更不會在開刀房「射刀」。陳景亮曾經問過李明哲,什麼他發飆也不會「丟器械」?李明哲說:「那多『沒品』。」因此,儘管李明哲是嘶吼也好、碎碎念也好,從來不曾出現「小李飛刀」。
「他自我要求很高,當然要求學生也高。」陳景亮說:「我們開到尾聲,『關傷口』時,就好像火車快到站了,大家都比較輕鬆,我們就開始跟他『抬槓』,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玩的『冷面笑將』。」
每週兩天的門診,其他時間就安排開刀,每個月六十到八十檯刀。李明哲常在一般外科手術後,如有器官捐贈者出現,他二話不說,飛奔去取器官,然後進行移植,連續手術下來,都是二、三十個小時。但是他無怨無悔:「病人的情況不允許等。我不做,誰來做?」
陳景亮問他累嗎?當然累!但是「開刀是一種信仰,不要問為什麼?」
「此生能遇見這麼好的老師,不簡單,很幸運。」陳景亮說。
病人買藥
稱李明哲為「老闆」的,除了陳景亮,還有施明蕙、社工張美茹、專師周桂君。她們一致認為李明哲的脾氣「很壞」;但也一致認為他「改善很多」了。
2001年九月,器官移植小組公開徵求一位協調護理師,當時任職外科加護病房的施明蕙表示願意承擔,讓許多同事都「跌破眼鏡」。
「跟著『李老爺』做事,妳不怕死啊?」同事她擔心。
結了婚,一心只想上正常班的施明蕙,也跟李明哲共事過,也曾挨罵過。但她認為他罵人是「對事不對人」,而且「罵過就算了」,還可以接受。如今三年多過去了,兩人相處和睦,培養出非常好的默契。
社工張美茹剛開始跟李明哲的接觸,因為彼此不了解對方的工作需求跟難處,總覺得格格不入。
如果有「潛在」的器捐者,李明哲會很急切,問張美茹:「家屬呢?同意了嗎?」但是站在張美茹的立場,要開口做器官勸募是需要時間跟因緣的。
直到有一天,兩人一起到台東參加「器官勸募中心」教育訓練的初階課程。她將自己扮演的角色和困難的地方清楚表白,當著李明哲的面,公開的說:「我以前很不喜歡李醫師,因為他都不了解我的困難......」引起哄堂大笑。
李明哲上台,劈頭第一句話就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以前我也很不喜歡張美茹,因為她也不了解我的困難......」
台下同樣哄堂大笑,張美茹更是拍案叫絕。就這樣,一笑泯恩仇,從此兩人跟施明蕙形成推動器官移植「鐵三角」。
李明哲的專師周桂君說,「老闆」再忙也會來巡房看病人,有時假日也會跑來。有的人傷口不佳,他還會親自換藥。
張美茹則觀察到他多次替貧窮的病人付醫藥費。原來東部很多原住民很窮,有些特效藥健保不給付,他們買不起,李明哲於心不忍,就自掏腰包付了。
「除了當醫師比較厲害之外,他啊,還真是笨,怎麼不曉得找我們社工。」張美茹忍不住偷偷罵他。
「當我知道美茹這一號人物,有許多社會資源可以申請時,我們的病人就有福了。」李明哲說。
可是為了器官勸捐,張美茹說:「因為我們的『節奏』不同,還是偶而會『對撞』。」
體會捐贈者家屬的難處
身為器官移植的專科醫師,李明哲的要求就是「快」!快點說服家屬,讓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同意捐贈。但是一個受贈者的變故,卻讓他對器官捐贈者家屬的處境感同身受。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課長蘇連勝,因腎衰竭洗腎幾年後,由李明哲?他做腎臟移植,因此建立了良好的醫病關係。儘管移植給蘇連勝的腎臟在運作五年後因慢性排斥而失效,讓他又開始洗腎,蘇家人仍對李明哲感激不盡。
2004年五月,蘇連勝的女兒蘇秀雯下班回家出了嚴重車禍,送到慈濟醫院已經腦死。
蘇秀雯畢業於慈濟護專,是鳳林榮民醫院護士。出事的前幾天,因為院內的一位榮民伯伯家屬說要捐器官,她因此和施明蕙、張美茹有過接觸。回家之後,蘇秀雯跟父母說:「如果人往生了,把廢物般的身體捐給別人,才有意義。」
豈料造化弄人,蘇秀雯一席話竟成最後遺言,蘇連勝夫婦只得強忍悲傷,送女兒最後一程。
「如果醫師沒辦法救她,就讓她去救別人吧!」蘇連勝夫妻想起女兒的心願,不約而同的,一個通知施明蕙;一個通知張美茹。等到李明哲接獲消息,他愣住了:「怎麼會?」
他到加護病房探視蘇秀雯,並激動的對蘇連勝夫妻說:「怎麼可以--再等等!再盡力搶救吧,或許有奇蹟出現--」一時間,不捨的心情全湧了上來,好像他自己就是家屬。
「以前若有腦死病人,家屬處在『捐』或『不捐』兩難時,我心裡都會想:『快做決定吧!再猶豫器官都要衰竭不能用了。』而面對從來不認識的蘇秀雯,我居然期待她還有一線生機。」
蘇秀雯終究往生了,因為心、肝、腎等器官衰竭得太快,都不能用了,她只能捐出心臟瓣膜和骨骼。
但或許是愛感動天吧,蘇連勝把女兒的器官捐出去後,又再一次得到別人的器官。九月,一顆非常配對的腎臟出現,李明哲再一次替他進行移植,使他成為東部第一位兩次換腎的人。
蘇連勝是受惠者,別人的器官延續他的生命;所以他也把往生的女兒捐出去,延續別人的生命。蘇家寫下了器官捐贈史上感人的一頁,而李明哲是最佳見證人。
追懷蔡蕙憶
而受贈者蔡蕙憶的往生,則讓李明哲深刻體會到「無力回天」的遺憾。人,終究不是「無所不能」。
「雖然蕙憶過世了,但我們還是感恩李醫師。」蔡蕙憶的母親徐麗瓊說。
蔡家三個孩子腎臟都有問題,老大蕙憶在國中時發病洗腎;2002年底,二女兒也步上姊姊後塵;最小的兒子則因症狀尚輕,僅服藥控制。
「兩個女兒真是多災多難,她們在洗腎的過程中還分別開了疝氣和副甲狀腺。」徐麗瓊說:「四次都是李明哲醫師開的刀,他技術好,待人親切,對病人就像家人一樣。」
2004年七月,洗腎室的護士打電話給徐麗瓊:「有一顆腎臟,跟蕙憶非常配對,您要不要讓她來換腎?」
「要!」徐麗瓊毫不考慮,立刻答應。「希望蕙憶換腎之後,可以不必忍受洗腎之苦。」
七月八日進行手術,李明哲告訴她:「非常順利。」蔡蕙憶甦醒後,開心的比勝利的手勢,和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打招呼。乖巧的蔡蕙憶,非常依賴媽媽,所以徐麗瓊也比一般家屬花更多的時間在加護病房陪伴女兒。
李明哲還跟蔡蕙憶說:「病房的電視都沒有卡通,下次我帶我兒子的卡通給妳看好不好?」他把十七歲的女孩還當成小娃娃。
「病人的變化,有時是出乎預料的。手術後第三天,蕙憶開始出現吸入性肺炎,雖然極力控制,還是快速的惡化。」
第五天,蕙憶心臟也出現衰竭,李明哲難過的告訴徐麗瓊:對不起,妳們要有心理準備。
徐麗瓊請在台中工作的先生趕快趕回來,心愛的女兒終於走了,夫妻倆痛哭之餘,也跟李明哲流淚擁抱。徐麗瓊告訴李明哲:「我知道你盡力了,謝謝你,這是我女兒的因緣。打起精神來,還有另一位換腎者需要你照顧,加油!」
寬容與遺愛
父母將蔡蕙憶的眼角膜捐贈出來;把學校送的奠儀捐做清寒學生獎學金。李明哲送來一個可愛的小熊維尼,和蔡蕙憶一起火化,一份心意永遠陪伴她長眠。
雖然有家屬的諒解和鼓勵,但是這件事還是讓李明哲幾乎崩潰,幾次在沒有人的地方失控痛哭,他反覆的想著:如果我再仔細評估、如果我再小心一點、如果我盡更大的力、如果......情況會不會改觀?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為什麼還有「脫軌演出」?原來,醫生不是神,也不是上帝。李明哲頹喪的,想著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就在眼前消逝,覺得不寒而慄。過去三、四十例成功移植的病人,讓他充滿自信。現在他深深體會到「戒慎恐懼」這句話裡的「恐懼」是什麼了。
徐麗瓊說:「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是愛我女兒的,沒有人想害她。洗腎室的護士自責的說,如果我不打電話叫蕙憶來換腎,蕙憶也不會死;李醫師更是久久無法適懷,這都是不必要的。對他們,我們心存感恩。」
身為義消女子救護隊的徐麗瓊,更能體會什麼叫做失去親人的「痛」。她迫不及待的填了器官捐贈卡,也向親友介紹器官捐贈,希望大家都能認同而加入器捐的行列。
有人建議徐家,向醫院或醫生討個公道。徐麗瓊說:大小的手術都有風險,沒有醫院或醫生想要害死人。如果動輒發生醫療糾紛,以後還有誰敢辦醫院?誰敢當醫生?
三個月後,徐麗瓊勇敢的再次來到慈濟醫院,參加器官捐贈追思音樂會。在那裡,遇見了李明哲,兩人緊緊相擁。一切,盡在不言中。
「有醫療仲介來找我們,想介紹二女兒到中國大陸換腎,被我拒絕了。如果要換腎,我們還是會找李明哲醫師。」徐麗瓊說。
器官受贈者的「同學會」
從台九線公路往南走,到了壽豐路段,就可以看到「富麗漁村」的招牌。這一天,「富麗漁村」餐廳客人不多,只有四對夫妻正在舉辦「再生同學會」。
「富麗漁村」主人陳威良說:「我們都是器官移植的受贈者,而且我們的器官都是來自同一個捐贈者。我們是『四位一體』。」
陳威良罹患肝硬化,在門諾醫院追蹤十年,後來情況越來越糟,醫師建議他登記換肝,否則不出一年,就會「走」了。
「我問過很多醫生,去哪裡換肝比較好?大家一致推崇慈濟醫院的李明哲,於是我就成為他的病人。」
2004年,陳威良接到施明蕙的電話,通知他有人器官捐贈,肝臟跟他很配,要他趕快來。
火速趕到醫院,他問李明哲:「換肝會有什麼副作用?」
「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死在手術檯上』。」李明哲說:「我必須確認病人移植的意願,並且明白告知可能發生的風險。」
陳威良看到李明哲的坦率,反而安下心來。賭吧!不冒險換肝也只剩一年的生命;醫生很有把握的神情,讓他覺得信心十足。
手術後醒來,陳威良慶幸自己還活著:「命撿回來了!我又重生了!感恩捐贈者、感恩慈濟、感恩李醫師......」
住院期間,接受同一捐贈者器官的四位受贈者(有些器官轉送到他院),彼此之間有一股微妙的親密感,因而成了好朋友。他們約定同時回診,分享近況。回診結束,常常帶著家人一起聚餐。
「我重生了,人生觀也不同了。我不再汲汲於賺錢,而是思索心生命應該怎麼過?」陳威良首先加入慈濟當會員:「我每個月把善款交給李超群醫師的夫人。」
陳威良毅然的把經營的網咖收起來,改成電腦教室,提供附近的學生來學習利用;規劃生態農場,利用五公頃的土地,開闢水生植物、昆蟲、鳥類棲息觀察區域。
2005年五月,「大愛農場」正式申請立案通過,他非常歡迎慈濟人來玩,他說:「我這裡有民宿、餐廳、蓮花池、生態觀察,最近還要蓋個迎賓館。」
七月,移植病友聯誼會就選在「大愛農場」舉辦,陳威良渴望百忙中的李明哲可以帶著妻兒來,看一看他蛻變之後的成果。
「他是一個懂得回饋社會的人。」李明哲欣慰的說。
感恩獻禮,無奇不有
器官移植,可遇而不可求。身為東台灣唯一器官移植醫師,李明哲八年來移植了四十多例腎臟和六例肝臟。他說,每一位移植病人都要和他互相「糾纏」一輩子。
「術後的追蹤輕忽不得,除了按時回診;舉凡要懷孕、出國,都要知會我一聲。我要評估他身體是否足以負擔?遠行時藥品帶足了沒?當地的氣候、衛生,都要考量。」
李明哲的對醫護人員的「嚴苛」是出了名,因為他說:人,是一條生命耶;不是捏陶土,捏壞了可以「重來」。但是對病人,他的「親切」也是出了名的。他喜歡跟病人談話,不厭其煩的回答各種問題。
病人把他當朋友,常常來看診時,會順手帶些土產來給他。面對淳樸的鄉下人的一番好意,常讓他感到窩心。
「剛剛採收的玉米、花生、釋迦、柚子......或是自己養殖的蜆仔、蝦子、鮮魚,還有茶葉、蓮花......」李明哲說:「有一個病人說,貴重的他送不起,送給我的是『全世界找也找不到的好東西』,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自己栽種的芭樂。」
收到土產,卻之不恭,李明哲會分享給診間的護士和移植小組的成員。施明蕙說:「有一次,一個病人送來一隻宰好煮熟的鵝。李醫師帶回去,塞在冰箱,『冷凍』了一年。」
原來那時李明哲的夫人蔡娟秀出國進修,他就搬到醫院單身宿舍住,把他放進冰箱後就忘得一乾二淨。
有人曾經送給他一顆南瓜,他帶回家,媽媽打開報紙一看說,這叫我怎麼煮?原來是一顆長得像南瓜的石頭。
「還有人從成功寄來活生生的龍蝦呢。」施明蕙說:「最好笑的是,還收到過一包『檢體』。」
那一天,診間一直有一股怪味道,門診結束後,才發現有一包塑膠袋裝著,裡面用報紙包得好好的東西。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包「檢體」。大家都笑翻天。
「那是個阿婆,護士要她下次來,帶大便檢體,送到二樓檢驗室。她大概弄不懂,就帶了一大包到診間來。」施明蕙說。
又捲又長的頭髮是李明哲的註冊商標,病人或家屬偶會遞上名片:「我在開髮廊,來我店裡,我幫你理頭髮,免費!」
病人李秋香換腎後三年又罹患癌症,臨終前要求見李明哲。她虛弱但清楚的說:「您是我最感恩的人,我最後一件事還要麻煩您:把我能用的器官拿出來,送給需要的人。」
李明哲含淚說:「以後,我們還會再見面的。」李秋香隔天凌晨過世,她捐出了眼角膜。
病人的回饋、家屬的支持,是李明哲無怨無悔堅持下去的最大力量來源。
莫讓生命在等待中消逝
「病人見到『老闆』,就好像見到『神』,『老闆』講的話,有如『聖旨』。」陳景亮說。
許多移植病人及家屬對李明哲抱著無限感恩的心,甚至視他如「再生父母」。但李明哲說:「我只是盡我當醫師的本分而已,沒什麼了不起。要感恩的應該是上人,和所有的醫療團隊。更要感恩的是捐贈者和家屬,醫師再厲害,也無法『變』出一個器官來呀!」
有些病人器官衰竭,必須移植才能活命。但是器官來源有限,許多病人在等待中死亡。
「以台灣一年一萬個洗腎者來說,一年至少需八千枚腎臟,然而目前國內一年捐贈腎臟的,約只有一百人左右。」李明哲焦急又無奈:「應該有更多有心的人一起來推動器捐的風氣,避免國人組團到國外去移植。」
美國的器捐同意是簽署在駕照上的;西班牙是全世界器捐最盛的國家,所有死亡的人一定要器捐或病理解剖;斯里蘭卡的眼角膜捐到全世界去,成為該國的一大特色。台灣應該急起直追。
肝臟移植已作六例,今年九月可申請活體肝臟移植的李明哲,即將在東部移植史上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病人移植後,從被照顧的人,變成照顧家人的人。家裡的活力又出現了,不但增加生產力,又可以減少醫療支出。」李明哲說:「慈濟照顧許多原住民和低收入戶,不失在東部蓋醫院的初衷;我也願意奉獻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給東台灣的民眾,不失我學醫救人的心願。」
冷靜的頭腦、火熱的心,配上精湛的外科醫術,李明哲用手術刀,刻劃了一個又一個愛與感恩的故事。他是器官受贈者的救命恩人;也是器官捐贈者無私大愛的見證人。
或許幾十年或百年之後,器官捐贈已是家常便飯。人們記得也好;遺忘也無妨,在慈濟,有一個外科醫師李明哲,他,是東台灣器官移植的先驅者;他,締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再生緣」。
代序2
另一種延續生命的方式 施明蕙
清晨五點,接到醫院總機轉來的電話:「施小姐,我是慈濟桃園分會的陳師兄,有個會員的家屬想要做器官捐贈,請問我們該怎麼做?」
天色朦朦亮的清晨,已經開始了我忙碌的一天。器官捐贈就是這樣,總是無法預期,隨時都會發生。
進入臨床護理工作已屆八年,然而真正接觸器官捐贈是在三年前。在外科加護病房工作的我,每天所見常是重症病危的患者,雖然人生終究一死,但真正面臨生離死別之際,誰能不悲傷,誰又能真正放下?
所以我很難想像,要有怎樣的捨得與放下,才能在這樣的時刻做下器官捐贈的決定?況且器官捐贈與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傳統習俗──「死後留全屍、八小時不可移動」的觀念,全都背道而馳;因此,這無疑是個需要勇氣與大愛的決定。但是,在肉體無法繼續運轉的狀況下,如果可以捐出有用的器官,讓等待移植的病患受惠,何嘗不是另一種延續生命的方式呢?
記得多年前,當上人在推動遺體捐贈時,父母親拿了他們的遺體捐贈同意書給我,要我藉著工作之便,送回慈濟大學。雖然當時我沒有正面的反對他們,但為了表達我不認同的心情,遂搪塞了很多理由,要他們以郵寄的方式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