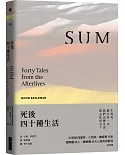一無所有的永恆革命
黃涵榆
這是一座牆的故事,牆內與牆外的兩個世界、過往、現今與未來、自我與他者的故事……「牆」是什麼?在哪?堙H空間的界線、時間的鴻溝、政體的敵對、理想與現實的斷裂、正常與異常的矛盾,抑或心靈的桎梏、自我的陌異……
不論是哪一派別的科幻小說──早期的硬式(hard science fiction)、軟式(soft science fiction)、新浪潮(new wave science fiction)、甚至電腦龐克(cyberpunk)──都在想像牆的那一邊有什麼;而牆那邊的異質體或對體(the
Other)──不管是太空船、外星人、異形、電腦病毒──也不斷進到牆內。科幻小說文類本身是一部活生生的「變形記」(其諸多派別,以及與其他通俗╱奇幻文類,例如:童話、英雄奇幻、恐怖小說、烏托邦文學等之交錯),就是異質體的具體再現。換言之,要為科幻小說尋求一種固定、封閉、排他的定義,是不可能的企圖;但是,我們接受一種涵蓋異質性的定義,亦即將「與對體的遭遇」視為科幻小說文類的共通特質。既是「遭遇」,便是一種想像、再現。想像╱再現一方面必然在特定意識形態框架中進行,是為外在現實的支撐;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撼動既定的現實感或對正常的界定,無法納入「正常的現實之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科幻小說批評家蘇文(Darko
Suvin)將科幻小說界定為「一種以陌異(estrangement)與認知(cognition)之交互作用為必要且充足條件之文類,其主要形式上之裝置為某種有別於作者所處之經驗環境之想像框架」。
科幻小說就文類特質而言,是矛盾的集合體;就再現的經驗而言,則反映出當代的科技、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等不同層次的矛盾,並提出想像的未來願景與可能的解決方案。一九七○年代集中出現的女性科幻小說亦不例外,重要作家包括卡特(Angela Carter)、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畢爾西(Marge Piercy)與魯絲(Joanna
Russ)。此陣營的女性科幻小說雖深具烏托邦色彩,卻比一般傳統烏托邦文學更突顯異質性或對體的存在。批評家莫依蘭(Tom Moylan)因而用「批判烏托邦文學」(critical
utopia)一詞稱呼此類揉雜科幻與烏托邦、對現時╱實歷史提出批判的小說。莫依蘭認為七○年代以來的批判烏托邦文學作品,再再不失烏托邦的未來想像願景,同時也表現出激進的差異性,清楚意識到任何一種烏托邦社會都有可能落入封閉的意識形態與妥協主義的困境裡。換言之,作品本身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作品世界中的矛盾衝突了然於目。我們不可能期待在這類小說中看到純真、伊甸園式、無限美好的樂園景象。牆就在那裡!活在牆裡世界的人可能不知道牆外還有什麼,甚至也可能抗拒知道有什麼。牆內與牆外──哪裡會有樂土,或是荒漠?如同勒瑰恩所著《一無所有》一開始的陳述,「這道牆如同所有的牆一樣曖昧,牆內和牆外的景觀完全取決於觀者站在牆的哪一邊」。
但是,牆也可能是一種流浪與探索的召喚。何以要離開?帶著什麼離開?到哪?堭敞薄H何時、何處才能落腳?能回家嗎?能帶著什麼回家?《一無所有》的主角薛維克來自一個施行共產╱社會╱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社會(安納瑞斯),前往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思維、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個人╱資本主義社會(烏拉斯)。「但是他沒帶回任何東西。他的雙手一無所有,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秤小說這樣結束。流浪者在牆內仰望牆外,跨越了阻隔兩個世界、過去與現在、自我與對體、理想與現實的圍牆,企圖拆解圍牆,卻又走進另一座圍牆(或監牢),雙手一無所有地回家。哪一個家?是安納瑞斯,或是從烏拉斯所觀視的安納瑞斯?或是超越疆界、並存於多重時間宇宙之中的的安納瑞斯.烏拉斯?小說不以直線式敘述,而是現在與過去交替跳躍,鋪陳出多重視野、不確定且曖昧的時空經驗。「事物會變化,變化,你不可能真正擁有什麼……你最不可能擁有的就是現在,除非你接受現在的同時,也接受過去和未來。不只現在,還有未來。不只未來,還有過去,因為它們才是真實的,只有它們才能讓現在變得真實」。「一無所有」指的難道不是慾望╱想像的空缺?「變得真實的現在」難道不是面對空缺╱創傷、「超越幻界」後的體認?這不都是保留自我批判動力、慾望流動、破除圍牆╱想像桎梏的必要的「主體匱乏」(the
destitution of the subject)嗎?
整部小說的敘述無不環繞在主角薛維克的「破牆之旅」。或許會有評論者批評勒瑰恩創造的薛維克,視其為典型的「偉大科學家」的化身、浪漫式童話故事的英雄人物、順服於以男性為主導的傳統性別價值觀。這樣的看法似乎沒有考慮到薛維克「(超)越(幻)界」的經歷。薛維克自始至終無法真正融入所處的大環境──同伴、學院、社會、國家──之中;強烈的孤寂與疏離感使得他終究還是向整個象徵體系(the
Symbolic)說不,抗拒(安納瑞斯與烏拉斯)既定的社會成規、語言邏輯、思維習慣、道德律法等。就最廣泛的層次而言,薛維克是「否定性」(negativity)的具體化身。然而,這種否定性是辯證的。我們先是看到薛維克個人否定大環境(或是「象徵體系」)。這種否定、對立、矛盾的關係是外在的、偶發的、立即的,還必須要有內在的自我否定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否定性的展現。換言之,如果說薛維克體現了任何顛覆、批判的意義,正是在於這種辯證的否定性,或是「否定的否定」(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薛維克信奉的歐多主義中,責任、忠誠、自由意志等道德原則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就此而言,真正的道德行為不在於遵守經驗層次的、體制的、外在的律法,而在於對超越的、普遍的律法的信念,有勇氣抗拒不公義的體制。而這種反叛是展現自我批判精神的其中一個階段。道德律法如不具有主體中介(mediation)的特質,我們又如何能有談論自由與責任的可能?政治、社會、文化、知識、心靈又如何能保持演化的動力呢?這不也正是歐多╱勒瑰恩所要彰顯的「批判烏托邦」的觀念嗎?薛維克的「破牆之旅」不也是為了實現這樣的觀念嗎?
整體而言,勒瑰恩在小說中建構的烏托邦是一種動態、永恆的革命,是一種未完成的進程、一種對於過往革命的失敗與空缺的體認。如莫依蘭所言,勒瑰恩「宣示了一種反抗集中化體制之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與永恆的革命。她讓烏托邦的動力得以存活,同時也反對任何烏托邦體制的停滯狀態」。勒瑰恩強調主體行動的重要:真正的烏托邦動力源於自我反省、批判的能力,或上述的「主體的匱乏」與否定性的展現。如傅里曼(Carl
Freedman)所言,「《一無所有》的辯證複雜性不應與拒絕選擇立場混為一談。事實上,勒瑰恩的作品並未陷入某種無政治主義,偽裝出一種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式的超越政治的立場。它之所以能夠以特殊的力量展現其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洞見,在於自我批判精神;這也是小說最大的成就」。
這是一座牆與破牆的故事……烏托邦在牆的哪一邊不是小說要回答的問題。或許,答案已經有了:一無所有,意義的豐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