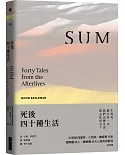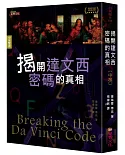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文╱楊茂秀
閱讀《踢豬男孩》,老是想找一句話來描述它。首先我想到的是:「這是一本鹹鹹的小說。」然後我又想到:「每一個人都是心存惡意的。」說它是鹹的,其實它也有苦味,也有澀味。細節的部分,酸的、甜的也不少。說他五味雜陳,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就小說來看,他是短小的。在成人世界,不管是小說的還是現實的,它都不是缺乏的。但是,給孩子看呢?別人如何覺得,我大概可以預料。但是我覺得,蠻好的。因為,它不討好大人,但是討好小孩。
英國著名兒童文學家C.S.路易斯(C.S.
Lewis)曾經說:「為兒童寫東西有三種方式:一種是投其所好的方式。他要什麼,你就給他什麼。另外一種是和小孩一起生活,了解他們的需要,就他們的需要提供給他們。第三種是把兒童故事當成是一種藝術的形式,有適合這種形式表達的東西,才去寫它。而他認為自己就是第三種。而《愛麗絲夢遊仙境》、《柳林中的風聲》、《魔戒》的作者是屬於第二種。許多流行的作家是屬於第一種的。」路易斯‧卡洛爾好像對第一種寫作的指導原則很不以為然。可是投其所好真的那麼不好嗎?我想問題不在於指導原則適當與否。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對人的吸引,是不是太過單純?或是太過複雜?如何恰到好處?好就是好。
實驗文學家葛楚‧史泰音(Gertrude Stein)曾經寫過一首詩:
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玫瑰是一種花。玫瑰可以是商品,是美感的對象。玫瑰也可以是植物學家研究的對象。玫瑰可以是愛情的象徵。可是當我們是一個個體,面對一朵花、一朵玫瑰花,認真去注視它的時候。是兩個具體存在單獨相會的時刻。它需要不斷的重新評估,一看、再看、再看。可是每一次看,結果都還是一朵玫瑰。這是非常簡單的事實。也是最難堅持的事實。
《踢豬男孩》這本書,我閱讀的時候,把他當個人一般,和他交談。它的插畫,是名插畫家David Roberts的力作。它讓我想到Edward
Gorey的作品。線條都短短的,營造?冷而硬的氣氛。但冷而硬卻又只是它的表象。它的文本夾敘夾義,一邊讀它,進入它的世界,背景卻出現了俄國大文豪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那是我教社會哲學和教育哲學的重要參考書。人,據說是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消失的話,生態的惡化就可以停止的唯一生物。如果宇宙不是以人為本的話,人其實是邪惡的動物。作為人的一份子,認真來看待這故事所呈現的訊息:
這個錯殺事件讓羅伯特更加肯定人類是很糟糕的,他討厭他們。他決定要與水獺、鯊魚、白鼬、毒蛇、老鼠、蟑螂和蜘蛛成為命運共同體。凡是人所討厭的動物,人愈想要消滅的動物,羅伯特就愈喜歡牠們。他決定要喜歡人類所憎恨的,同時並憎恨人類。不過雖然他討厭人類,他還是找到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來掩飾心中的憎恨。
從這方面來看待這本書已經落入以價值為基礎的判斷系統。一開始,我就覺得,太過單純的判斷,廣告的成分,會傷到了解的基礎。閱讀的過程中,它讓我回想起自己小時侯的經驗:我曾經也很喜歡踢東西。在路上碰到罐頭、好踢的一粒石頭、樹枝、果子,多半會抬腳踢它一下。小孩為什麼喜歡踢東西?誰知道?這裡面應該沒有什麼惡意或善意,甚至連目的也沒有。
小時候過年的時候放鞭炮,有朋友把炮竹放在牛糞上。炮聲一響,滿天大便。圍觀的人,大家快樂。有人也要放,有鞭炮的人就是不給他放。終於給他放,但是當他把炮竹放在牛糞堆裡時,偷偷的把火藥芯剪得很短。點炮竹的小孩沒有注意,點著點著,我們大家都跑的老遠。炮聲一響,他炸得滿臉牛糞。我們大家都好快樂。點炮竹的小孩,又哭又笑。我們真是要害這個小孩嗎?或者我們不知道自己其實是那麼邪惡的?
這是一本容易引起有關人性討論的故事。我有朋友說:「這是可以隨時停下來,隨時重新開始讀的小說。」我自己則是翻開就難以停下來,非把它讀完不可。我覺得讀一遍是不夠的。我認識一個小孩,非常喜歡小說。可是我發現她的好多書,讀到最後,快結束的時候,就停止了。問她為什麼,她說:「太好看了,我捨不得把它讀完。」而《踢豬男孩》,最後的結局,蠻噁心的。而那種噁心,會使你想要從頭再看一遍。它讓我想到日本詩人水村一美的《我是一隻蟋蟀》書中的最後一首詩。在介紹了十二種虛擬的表達人跟人之間,最普遍和深沉的愛之後,這樣寫:
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用來說
我愛你,
但是,我只是微笑,
請你自己去體會:
我是在愛你。
我常常在演奏這首詩的時候,建議人家試一試把詩中的「愛」改成「恨」。它就成了:
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用來說
我恨你,
但是,我只是微笑,
請你自己去體會:
我是在恨你。
多麼可怕呀!不是嗎?《踢豬男孩》似乎用小說的,散的方式,呈現出人愛與恨、善與惡的一體兩面,認真想來卻是很多很多面,而且面面都五味雜陳,使人想再吃一遍。
(本文作者為台東大學兒童文學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