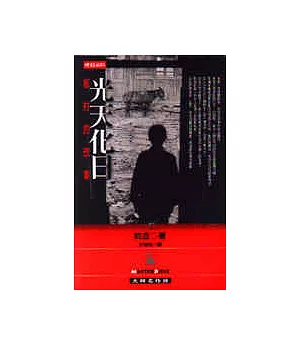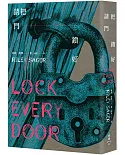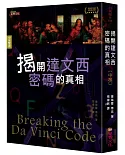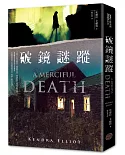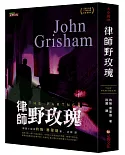亮甲店是遼寧省金縣的一個小鎮。三四十年前鎮上只有幾條短街,三五家商店,但卻很熱鬧。從大連通往城子坦的鐵路打這裡經過,鎮上也通汽車。此外,鎮東邊有一大片營房,裡面多是二層磚樓,終年駐紮著一個師的總部和數百家軍官家屬。營房是為蘇聯軍隊在 50
年代初建的,所有設施都挺現代的,還有一個奧運會標準的大游泳池。「歇馬亭」基本上是以亮甲店為原型的,但我寫的是小說,必須有想像的空間,所以有些地名、街名是虛構的,有些事件是從別的地方搬過來的,是為了把故事寫得豐富堅實。
60
年代初,我父親是駐在亮甲店的一個通訊營的政委。他級別較低,所以我們家不能住進師部那片大營房裡,只能住在街頭的一個小院子裡。這樣,我們兄弟們就跟街上的孩子們混在一起,打成一片,所以我對鎮上老百姓的生活比較熟悉。後來部隊換防了,我們家搬到了庄河縣。上大學後,我去過亮甲店兩次,覺得這地方真是太小了。當年的頑童們都長成大人了,可是似乎在心理上並沒有多大成長,他們還在談著打架吃酒之類的事。不管怎樣,我對那個小鎮是深有感情的。我在那裡生長了
12 年,幾乎整個童年都在那度過。來美國後,常常想起那個地方,也許小鎮上的許多東西都已經消失了。在某種意義上,我寫《光天化日》是為了把一些曾經在那裡存在過的人和事物保存在紙上。不管是嚴酷的,還是溫暖的。
這是一本真實的書,沒有任何事件是虛構的。做為一個作家,我所做的不過是重新編整結合人物和細節,將其安排進「歇馬亭」和它附近的村子裡。在結構上《光天化日》深受喬依斯的《都柏林人》和安德生的《俄亥俄州溫涅斯堡》的影響: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地點,有些人物在不同的故事裡重複出現,每個單篇都起著支撐別的故事的作用,整個書構成一部地方誌式的道德史。但《光天化日》寫的不只是一個地方,也是一個時代。
這是我的第 2 本小說。94 年寫完後到處投送,但無人願意出書。幸虧喬治亞州立大學出版社於 96 年接受了這本書,才使 4、5 年的勞動沒有白費。
96 年底,我的一位朋友比爾.霍姆斯(Bill Holms)請我去明尼蘇達州的西南大學去朗讀作品。那所大學在馬歇爾城,遠離都市,馬城連個客運機場都沒有。電話上比爾對我說:「我派一架飛機去蘇佛斯接你。」第二天,我到南達科他州的邊城蘇佛斯後,等了兩個小時也不見什麼專機。下午 3、4
點鐘,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伙子出現了,他們把我拉到一架契克威勇士型的小飛機旁,機裡只有兩個座位,實在太小了。更令我吃驚的是那個名叫安文的 12
歲的孩子是飛行員,而那個敦實的小伙子只是他的飛行教員。沒辦法,又不能不去,我就隨他們入機上天了。一路上搖盪顛簸,晃得我心魂不安,不得不想起自己的「後事」,想起家人和一些掛在心上的事情。令我驚訝的是,當我想到剛剛寄出去的、修改過的《光天化日》的校樣時,心裡十分坦然,覺得這是一件完成了的事,怎麼想也想不出還該做什麼,想不出有那個詞或標點該改一下。的確,為這個短篇集子我真的盡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說,就這本書來講,當時是死而無憾了。
我很高興,王瑞芸的準確生動的譯筆能將這些故事呈現給台灣讀者。不管它們令你悲哀、或震驚、或沮喪,這裡所描敘的不過是千百萬大陸上的中國人曾經經歷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