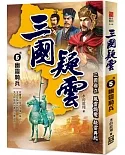我們一開始租下的公寓,是一個非常小巧美麗的房間,廚房、浴室是一個個大壁櫃,要用時拉開來,用完門一關上便都消失了。
因為家中的活動空間太小,跟荷西彼此膩了時,另一只有到陽台上站著看山看海看風景去。
又有時候,日子本來得好好的,竟會為了誰在這個極小的家裏多踩了誰幾腳,又無聊的開始糾纏不清,存心無賴吵鬧一番,當作新鮮事來消遣。
這種擁擠的日子過了三四個月,我打聽到在同一個住宅區的後排公寓有房子出租,價錢雖然貴了些,可是還是下決心去租了下來,那兒共有兩間,加上一個美麗的大陽台對著遠山,荷西與我各得其所自然不會再步步為營了。
搬家的那一日,我們起了個早,因為沒有笨重的家具要搬,自然是十分輕鬆的。
當荷西將書籍盆景往車上抬的時候,我抱起了一大堆衣服,往不遠處的新家走去,幻想著,在這陽光和煦的春日裏,我正懷抱著一大批五顏六色萬國旗,踏著進行曲,要去海灘佈置一個節日的會場。這麼一亂想,藍得更美麗了,搬家竟變成了驚人有趣的事情。
當我拖拖絆絆的爬上三樓,拿出鑰匙來時,才發覺新家的房門是大開著的。
客廳裏,一個斜眼粗壯的迦納利群島的女人扠腰分腳定定的著我,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嘴巴微微的張著,看上去給人一種癡呆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