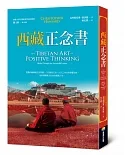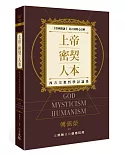臺灣地區的宗教信仰相當的多元豐富,不僅儒釋道耶回五大宗教並存發展,還有生命力旺盛的各種民間宗教與信仰活動充斥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個眾聲喧嘩的宗教世界,如果將臺灣形容為一個「宗教的百貨櫥窗」當不為過。面對這些紛然並立的宗教信仰,該如何去理解,學界依其不同的學科與方法進行探討。和社會學科長於理論建構相較,歷史學更著重於實證研究,並依此掌握其常態與變化之跡象。近年來,臺灣學界的兩位新銳王見川、李世偉依此路徑進行臺灣的宗教研究,並取得可觀的研究成果。
王見川目前為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也是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專任講師,他很早便自學成精,在中國民間宗教的領域上縱橫俾闔,引人注目,其碩士論文《從明教到摩尼教》甫一出版便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爾後更著有《臺灣的齋教與鸞堂》、《高雄縣教派宗教》、《雲林縣發展史------宗教與社會》、《臺南德化堂的歷史》,另外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臺灣齋教的歷史與展望》、《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的探索》、《民間宗教》(雜誌)等,著述甚豐,頗受好評。李世偉為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目前為花蓮大漢技術學院及淡江大學歷史系助教授,有《中共與民間文化(1935-1948)》、《日據時代臺灣的儒教結社與活動》二書出版,其著作以其研究視角獨特、取材豐富、文筆優異而為專家所稱道,目前致力於華人地區儒教文化、民間宗教與近代佛教等相關課題,並主編《臺灣宗教研究通訊》雜誌。這次由博揚文化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臺灣的宗教與文化》一書是王、李二人近三年的研究成果,內容涵括儒、釋、道三教,以及民間文化,時間從清末至戰後。這些文章先前曾在各個學術研討會或學術刊物中發表過,部分內容也引來不少的爭議與討論,但大體而言,他們的論述是可以經得起考驗與檢證的,也歡迎各界的批評指教。
本書的特點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四點來談:
一、資料豐富詳盡:眾所週知的,歷史的論述是以史料為基礎的,新史料的出土與運用也將成就新的論述,民初國學大家王國維在一次的演講中曾說過:「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此話或有誇大之處,但新史料的問世得以拓寬研究者的視野卻是無可置疑的。宗教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國亡佚而於日本保存的唯識學文獻的重新傳入,刺激了佛學研究的新境界;敦煌佛學、道教、摩尼教資料的發現則改變了過去宗教史方面的舊說;清宮檔案的公佈與明清寶卷的搜集開拓了近代民間宗教的新領域。
作者所開發運用的史料,以及因此作出的論述,固然不能與這些前輩的成就相提並論,但對於臺灣宗教發展的釐清與再認識是有相當助益。大體而言,書中的論文大量地運用官方檔案、報紙、期刊雜誌、方志、善書等資料,在書中附有一篇<光復前(1945)臺灣鸞堂著作善書目錄>,是目前相關書目資料最完整的介紹。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日日新報》的運用,這份日據時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內容包羅萬象,除了例行性的官方通告與新聞外,裡面大量的刊載許多宗教、民俗、戲曲、游藝等活動,對於了解當時的庶民社會與文化有必然的助益。這二本書的絕大多數論文都充分的運用這分資料,也藉由這分資料獲得許多突破性的發現,讀者細讀後當能有所體會。
二、考證精確詳密:歷史論述必須立基於可信的史實,因此對於史實的辨正分判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夫,王、李二人皆有出色的表現,尤其王見川更被臺灣知名的佛教學者江燦騰譽為:「目前關於宗教文獻收集和考辨工夫,以同年齡的表現相比,實超越近代最富盛名的宗教學者陳垣先生」。本書中,作者建基在大量的開發史料上,展開周詳細密的考證工夫,澄清了許多宗教史上的疑團或誤解。例如西來庵一向被視為齋堂,「西來庵事件」也多被凸顯其政治意義,但有關宗教意義的討論一向薄弱,我們經由報紙、鸞書等資料的分析與理解,才知道西來庵其實是一個鸞堂。而「西來庵事件」發生後,促成了日本當局大規模的宗教調查與臺灣宗教界的聯合組織(參見<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一文)。
三、研究視野寬闊:除了循一般宗教史的研究路徑外,作者也希望能開拓一些過往為人所未嘗留意的課題。然而,作者並非刻意要標新立異,專走偏鋒,因為這些研究課題不單是在臺灣宗教史上,甚至在社會史、文化史都有極重要的地位,只是由於種種原因,被學界長久的忽視罷了。茲舉一二例子略做說明,儒、釋、道三教一向並稱為中國的主要宗教,但對於儒教的討論,始終圍繞著「儒家是否為一宗教」打轉,其研究課題也多半局限於儒教領導人物的思想、經典、事蹟,未見其餘。殊不知臺灣在清末以來已發展出明確宗教型態的儒教結社,其中尤以鸞堂為著,李世偉在「儒教篇」的相關文章對此探討頗多,並放在中國近代儒教宗教化,以及華人地區孔教結社的脈絡來看,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讀者可自行參考。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各個宗教的交涉互動,中國社會對於宗教的觀念一向寬鬆,加上臺灣由於諸多內外環境的影響,各宗教間相互交涉的情形是相當普遍的。例如清代以來,有在家佛教之稱的齋教原本便與佛教關係密切,日據時代幾個重要的齋教領袖如黃玉階、廖炭、許林等皆與佛教相善;又因為齋教的勢力極大,許多佛教界著名法師均因齋教而得以親近佛緣,如善慧、妙果皆出自齋教龍華派。又如日據時代許多鸞堂的鸞生,同時也是詩社的成員、書房的教師或善社的宣講生,這些看似複雜的角色也不難理解,因為他們多是儒教的信徒與傳統漢文化的支持者(參見<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這些課題對於開拓宗教研究的視野應當是有所助益的。
四、選題別出心裁:作者在本書中也企圖開發一些新的研究題裁,提供學界加以思索。例如目前社會人文學界相當熱門的「認同」課題,過往研究者多汲汲於從政治、族群等面向討論,而作者卻另闢蹊徑,從宗教的角度切入,探討日據時代的台灣佛教,在殖民統治下面對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如何肆應與選擇。作者認為佛教界的認同與一般知識分子不同之處在於,知識分子或一般社會領導階層可以根據個人的思想、立場而作認同上的選擇,但佛教界必須考量整體僧團和教界的生存發展,個別自主性較弱。日據時代,經過現代化改革的日本佛教雖然有其吸引人之處,但其肉食妻帶的特質則難為臺灣所接受,故許多修行方式還是保留中國大陸的模式,加上太虛法師的改革理念逐漸獲得臺灣教界的認同,遂得以維繫中國佛教的基本特質,其論述深刻可信,值的玩味再三。(參見<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的認同與選擇──以中台佛教交流為視角>一文)。
臺灣宗教史的研究在九十年代的發展,不論在質與量上都有顯著的提昇,新的研究視野、方法、資料不斷推陳出新,新進的研究者也竭盡所能地逞其屠龍之術,其研究成果相當可觀,也自然強烈地衝擊傳統的宗教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也是九十年代最後一年呈現此一著作,未必會帶來什麼世紀末的震憾,但對於臺灣宗教史的研究絕對可以帶來一番新氣象,期待識者方家不吝口舌筆墨,多多提出批評指教。